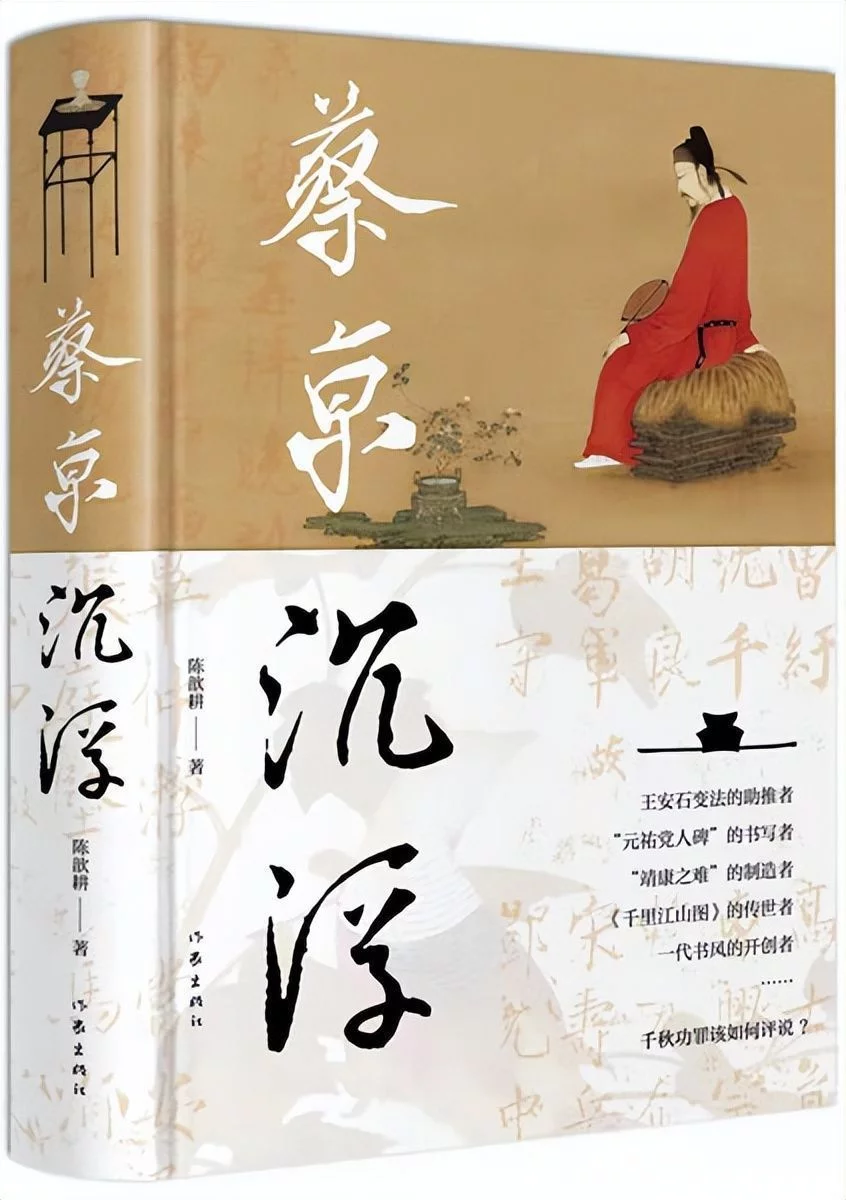对于已有定论的历史反面人物,学者一般是不会轻易触碰的。一方面,这些人在世时便名声不好,是居庙堂之高的奸佞权臣,往往专权擅势、奸诈贪婪;处江湖之远的鸡鸣狗盗之徒,更不值得书写。而对于前者,即便花费心思研究,其成果却有限,甚至会落得吃力不讨好的结局。
北宋时期的蔡京,便是一个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。《宋史》将蔡京列入《奸臣传》后,对蔡京的评价一直是徽宗朝“六贼之首”。早在北宋末年太学生陈东上书,将蔡京列为“六贼”之首,“贼名”就已成了抹不掉的符号。其人阴险狡诈,惑乱人主,结党营私,倡导“丰亨豫大”,致使民不聊生,以上任何一条罪名,都令蔡京脱不了一代巨奸的恶名,何况传统史学界一直把蔡京定为北宋灭亡的千古罪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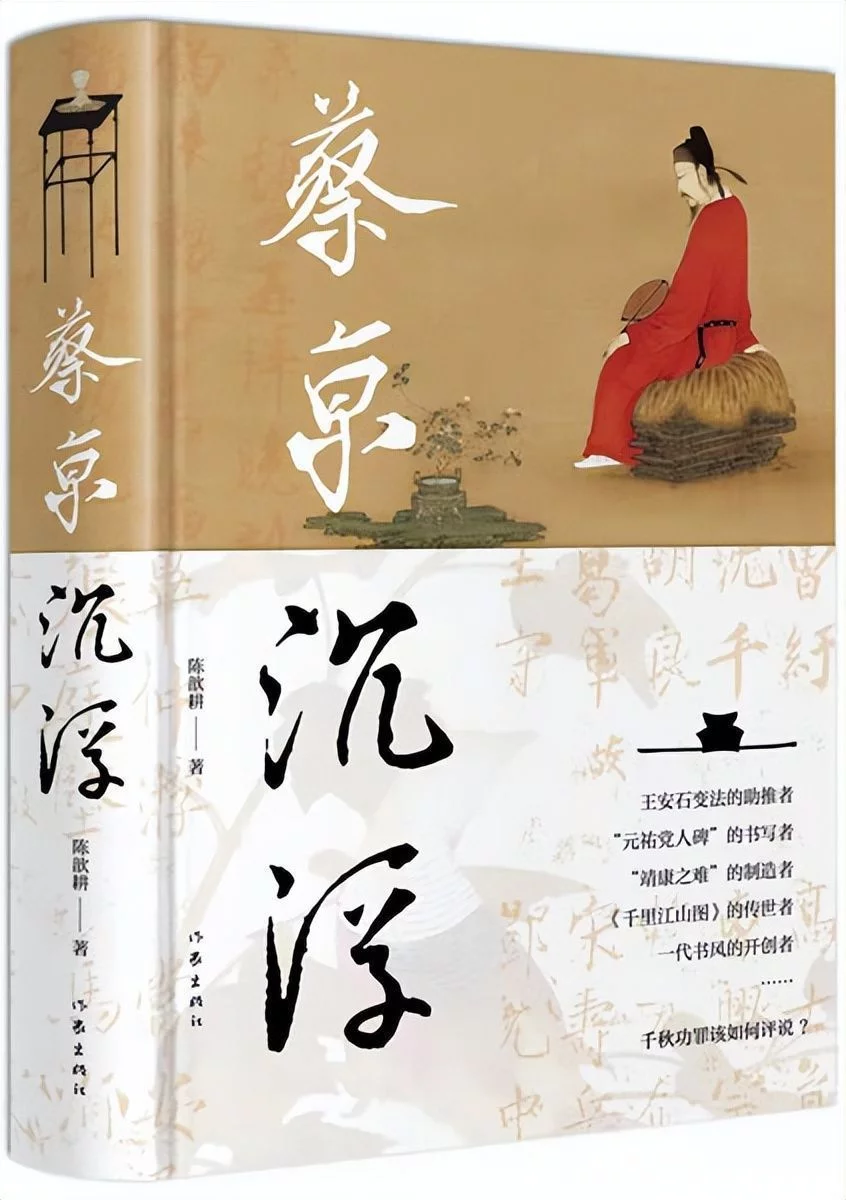
文化学者陈歆耕先生将其“作为一种特殊官场人格标本”,在“花时间和笔墨做较为精细的考察和解剖”过程中,摒弃一些史学家和文人将人物标签化、脸谱化的做法,不简单作非此即彼、非“忠”即“奸”的判断,在新出版的《蔡京沉浮》一书(作家出版社,2022.3)中,将蔡京当作“扁平人物”与“圆形人物”的复合体,为读者呈现出其人格元素的丰富性和复杂性。
事实上,宋朝就是一个纷繁复杂、饱受争议的朝代。“没有哪个王朝像宋王朝拥有星河般璀璨的诗文大家,也没有哪个王朝让人感到特别地‘窝心’‘糟心’‘痛心’。”特别是宋朝历史上很有名的“党祸”非常严重,甚至立“元祐党人碑”,连苏轼、苏辙等名声显赫的人都列在碑上,遭到贬黜迫害。另一派的王安石也是如此。历史上对他评价不一,甚至时有诋毁,但却说不出他所谓坏的事实,只是说他的变法不对,或是想法虽好却不合时宜。
封建社会的官场上,人格往往是分裂的,好人做不了好官,好官又做不了好人,一如蔡京本人所言:“既作好官,又要做好人,两者岂可得兼耶?”身在官场,四度为相、浸淫官场数十载的蔡京,见风使舵、玩弄权术,在权力斗争中心毒手狠、置对方于死地,就成他主要“官场人格”特征。
比如崇宁元年(1102年),56岁的蔡京在官场几经沉浮、磨炼数十载,政治手腕已炉火纯青之时,登上了副宰相高位。这年6月,宰相曾布向官家推荐陈祐甫任户部侍郎,嗅觉高度灵敏的蔡京,立马抓住把柄弹劾曾布,因为陈祐甫与曾布有姻亲,陈祐甫之子陈迪乃曾布之爱婿。故而曾布涉嫌“以爵禄私其所亲”。曾布未料时为翰林学士的蔡京来这一手,声色俱厉地在皇上面前为自己辩护,无奈与陈祐甫的亲家关系无法“辩”掉,没几日曾布被罢相,蔡京上位。蔡京在整个事件中,就如写字用笔“何时该方,何处该圆,何处先方后圆,何处先圆后方,何处方圆兼济,可谓随心所欲、得心应手”。
登上首相的蔡京自然处处揣摸皇帝意图,用尽心机迎合取悦。即位不久的徽宗,颇有明君之气,试图干出一番事业,有意恢复其父神宗的改革举措。此时,深谙政治投机之术的蔡京,马上打出辅佐徽宗“上述父兄之志”、恢复“新法”的旗号,但仅此而已。对“诸事皆能,独不能为君”的徽宗,身为宰相的蔡京,本该全力辅佐,劝谏徽宗以国事为重,但蔡京出于个人目的,投其所好,听任他沉湎于声色犬马,辅佐者成为操纵者。为更方便操纵徽宗,蔡京甚至在宫内布有内线,随时获知宫中信息,把握徽宗心思,知晓政敌动向。
这与王安石形成了鲜明对比。王安石在宰相之位推行新法后,两次裁减皇室后妃公主及相关人员的赏钱和推恩钱,甚至在《裁宗室授官法》中,要求大量减少皇亲通过恩荫不考而直接获得官职,这近乎往皇族及子孙胸口插刀的做法,自然让王安石得罪很多人,皇室自不多言,朝廷的“墙头草”更是会伺机随时给予王安石致命一击。而蔡京恰恰相反,他从“摆平”皇帝入手,继而“摆平”一切,为所欲为。王安石推行《裁宗室授官法》,不惜得罪皇室宗亲,蔡京则“睦九族”,谁更容易得宠可想而知。特别在掌握行政、军事、财政大权后,对内横征暴敛,贪财纳贿,对外兴兵黩武,轻起边衅,以致刘子翚评其“空嗟履鼎误前朝,骨朽人间骂未消。”老百姓更是恨之入骨。蔡京在京师为扩建府第,毁民房数百间,被贬后,即被百姓放火烧成灰烬。 难怪陈歆耕先生感叹,“无论怎么客观评价蔡京,其人‘巨奸’‘巨贼’的罪愆是洗刷不掉的。”
然而,在一个道德意义上的“奸人”背后,其精明强干的行政能力和目光超前的经济制度设计,确实是蔡京掩藏不住的一大亮点。蔡京主持的对茶、盐、酒等专卖领域的经济改革,对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产生深远影响,成为经南宋直至元明清沿用的专卖制度的范本。货币改革也适应了社会各阶层对货币的需求,社会救助制度的推行力度之大,包括其书法艺术,亦有可圈可点之处。这也使得治世之才和奸佞权臣双重形象,在蔡京身上“矛盾”地重合起来。
其实,观照历史不难发现,这种情况并不鲜见。历史上很多“奸人”都具有超乎寻常的能力,以致“奸”本身也成为一种“能力”。都说“人之初、性本善”,但究竟为什么在特定时代,能力越强的人会越坏,说到底,不好的制度能逼人走上邪路,把好人变成坏人,反之亦然。不过,把个人的品德皆归于所处时代则也有失公允。在历史的长河里,总有一些人能够不断自我净化、自我升华,即便在蔡京所处时代,范仲淹在地方治政、守边皆有良好政声,所倡导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思想和节操,更为后人所称道。
陈歆耕先生把蔡京作为“官场动物”标本,考察和解剖其“超常的官场生存能力”,目的是“客观解析其人其事折射出的官场生态、人格元素”,以“触发更多的政治、经济、历史、文学的多元思考”。读罢《蔡京沉浮》,深感作者事随人愿,艰辛笔耕,收获颇丰。作者以批判的眼光、理性的笔触,考察和剖析了蔡京的一生,让读者对北宋那段历史有了更加形象的认识。同时,《蔡京沉浮》也有别于冰冷的正史,闲暇之余或随手翻阅,或仔细研读,可以轻松地了解历史、引发遐想。(苏虹)